王璜生生命是一种偶然与必然艺术则是对生命本质的追寻

艺术家王璜生
导语:
2024年4月,“王璜生:七重旅途”暨“从这里出发:珠江溯源记(1984-2024)巡回展”在王璜生家乡的汕头美术馆举办。展览包含了他近年来创作的装置、绘画、影像、水墨等作品,以及围绕40年前珠江溯源的写生创作,涵盖艺术家艺术生涯多重维度。
“珠江溯源记”巡回展览的起因是王璜生在28岁那一年的“珠江溯源”骑行。1984年,王璜生和好友李毅从家乡汕头出发,背着相机、速写本、画板和睡袋,骑着二八自行车,途经珠江入海口,横贯珠三角的河汊村野,深入广西的荒山老林,穿越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骑行70多天,行程3300多公里。在艰苦的旅行中,王璜生沿途拍摄七八百张照片,画了近100幅画,给初恋女友写了9万字的信件日记。这些摄影胶片、绘画图像及记述文字,构成了一部80年代初期的珠江人文地理视觉考察志。王璜生在日记中描绘珠江:“它不仅秀媚而且充满野性和活力。”

河滩的路,摄影:李毅 135mm 黑白负片
王璜生早年的珠江溯源行动并非预设了多少目的和意义。但这一段充满波西米亚色彩的文化旅程,正是王璜生多年后作为艺术家、美术馆管理者、博物馆与艺术史研究学者等多重身份背后人生信念的映照:独立、坚持、挑战自我、不拘一格,勇于突破边界。
在2020年疫情的慢生活中,闭关居家的王璜生偶然打开被遗忘在抽屉角落的日记本,那段尘封了36年的记忆重新被唤醒,他惊讶于自己当年的勇敢行动和留存的丰富历史资料。就这一年,王璜生重返珠江源,延续了1984年的采撷行为,收集了珠江源的植物标本,并将这些标本转化为影像、绘画,随后又创作了多件大型装置作品。这些作品与早期的“珠江溯源”图文日记共同构成本次巡回展的核心内容。
近日,王璜生接受了“艺术中国”的专访,深入解读了青年时期的“珠江溯源”行动及巡回展中的当代艺术创作。


珠江溯源·路途艰辛
珠江骑行,为了寻找心中的橄榄树
艺术中国:80年代中国有很多围绕黄河长江的漂流或行走的事件,您的“珠江溯源”的方式更艺术化一些,您的这种方式源于哪些因素?
王璜生:那时候大家谈到长江和黄河,往往是以母亲河等的形象作宏大宣传。我们没有那么崇高的野心和期待,当年只是想沿着身边的大河——珠江骑行走走,既是对自己的青春有一种锻炼与交代,也美其名“为了寻找心中的橄榄树”。
这件事起因可能有好几方面。首先有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之初,尤其是在1981年左右,在汕头那样偏远的小城市里有一群搞美术、文学评论、诗歌、摄影的年轻人,经常会有一些交流、讨论及活动,大家都渴望跟外界接触,了解更多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艺术、文学和诗歌的形式,大家都希望能感受到新文化的气息。
第二就是高考,1979年我开始参加高考,但是一直落选。1983年底我再次报考研究生,但是1984年初连准考证都没用给我。失望之极,我便跑到海南岛五指山中,在一个只有21户人家的黎族村庄里和黎族村民一起过年,我清楚地记得正月十五晚上我睡在尖峰岭原始森林巡林员的简易棚里,欣赏那满天的月光和黝黑的树影。
还有一个原因是工作。1970年到1973年我随父母下乡回到家乡,1974年回城在街道的机械工厂工作,后来也变换了几个工厂机构等,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参加高考。到了80年代初,所在的特种工艺厂经常停发工资,我也便有时间和理由出来到处逛逛。
还有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情感问题。我一直到28岁才有所谓的初恋,也正因为刚刚初恋,又马上跑出来“珠江溯源”,才有了在骑行路上每天给自己的初恋写一封信,两天寄出一次的行为动力。虽然这一路经过的地方有时候很偏僻,但奇迹的是这些信都寄到了,后来也被保存下来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我将太个人情感化的部分隐掉了,变成了“日记”。

珠江溯源·日记手稿


王璜生的部分1984年水墨写生作品

珠三角夕阳 纸本水墨设色 69x64cm 1984
艺术中国:《王璜生:珠江溯源记》巡回展完整呈现了您当年在珠江骑行中留存的丰富的视觉和文字,不同于一般艺术生的绘画写生,您的珠江地理行走有田野记录的文献性,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璜生:我觉得巡回展主要还是体现80年代初我们这代人在茫然中寻找突破或者追求自己独立性的一种冲动和行动。当年我们以骑行的方式,通过自己的拍摄、画画和9万多文字记录了这一历程。
我觉得有几点比较有意思。一方面当年的文字记录了80年代初我的观察和思考,观众能看到那个历史年代年轻人怎么看社会看现实,虽然现在看起来有些幼稚,但也很真实。

珠江溯源·银盐摄影(黔江渡口)

《珠三角河汊》,纸基银盐,27.5x18.2cm,1984年拍摄 ,2020年冲印

带浮标的小孩 纸基银盐 27.5x18.2cm 1984年拍摄 2020年冲印
第二,摄影部分比较真实地记录了80年代初珠江流域的一些人文和自然的景象。虽然我没受过专业摄影训练,当时的拍摄也没有很强的目的性,但是无心插柳的拍摄记录,更自然地反映了历史的情景。更难得的是这样的记录图像还都基本保留下来了。
艺术中国:您提到了80年代初的时代背景,当时中国很多城市里都有文艺青年发起的诗歌、绘画和摄影等活动,您认为这些活动对您的艺术创作有哪些潜在影响?
王璜生:我认为这些方面使我的综合性艺术创作思想更加成熟,包括对文学诗歌,对社会的敏感表达等。现在我使用纱布、铁丝网等媒材进行当代方式转换的创作,来自于一直注重于社会现实的表达。80年代初我画过国画、油画等的人物画创作,主要关注贫困山区、底层人物的题材。我画过一张油画,题为《一封寄往遥远地方的信》,画面是山区里一个穿着破衣服的光小孩,在村头一个破旧邮箱前,踮着脚将一封信艰难地投进邮箱。当时我刚去过三峡山区深处写生,深刻感受到那里儿童生活的艰辛,他们渴望与外面的世界产生关联,也对未来充满着期盼。因此我创作了这张作品,自己特别喜欢,但是这张画后来不知放哪里去了。我当时还画了一些类似题材的画,如《山伢子的歌》《老舅与帆》等。

老舅与帆 纸本水墨设色 205x145cm 1985年
艺术中国:“珠江溯源”对您后来的人生经历有怎样的影响?
王璜生:现在大家认为我们当年的骑行事件意义很大,但当时我们对这事并没太当回事。我和我同行的李毅,画油画的,都是面对种种的高考失败、情感问题及青春不安等等的困境,我们希望在压抑沉闷的状态中通过出走的方式寻找另外一个新世界。
而现在重新回头看这事,确实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后来我做美术馆的工作,也包括为人做事的方式,多多少少都离不开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包括做事的规划,知识的准备,到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如何不断面对各种挑战,怎样将一个事坚持做完等等。
重走珠江,寻找30多年的变与不变
艺术中国:很多艺术家都喜欢原生态的旧事物,但您对新旧变化更为豁达,当您重返珠江源头主要关注了哪些地方?有哪些变化令您感到遗憾或欣喜?
王璜生:2020年、2021年我两次返回珠江源头,首先是寻找当年骑走的痕迹和感觉。第二是观察这一路的变化。30多年过去了,现实一直在改变,我们寻找这样的变化在哪里。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有”变成“无”,而“无”变成“有”,这是循环往复或者递进的关系。不能说当年老土,原汁原味的东西绝对就是好的,当年一些这样的传统东西、原始民俗风物的东西,如今没有了。当然有令我感到很多遗憾之处,很多地方将传统事物转换成新东西时,那种原有的审美感,隐含的仪式感,深厚的文化内涵等,都给丢失了。

1984年的燕来村立房子
比如,我在珠江溯源日记里记述了当年我们在广西西北部的燕来村的经历。当时我们经过燕来村正好赶上一家人建房子。建木头房子需要搭建主木梁,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大事,也是村里很有仪式感的活动,房主会招呼四乡八邻的亲戚朋友过来帮忙,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前一天晚上大家聚集在村里,热热闹闹地喝酒唱歌。一直闹到天将亮,这时,大家就“合力”拉架子把主梁竖起来,非常有仪式感,情感凝力聚也很强,大家都很享受这一过程。

今天的燕来村
这次我们重返珠江时看到路标上有“燕来乡”的标识,就开车去寻找。一路土石烟尘,村子已经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水泥房子。当地人告诉我们当年的燕来村并不在这里,而是在20来公里外新建水库的水下几十米处。当年村子搬迁,村民们急匆匆乱建了一通“现代水泥房子”,非常遗憾!当年那些建筑精美考究的木头房子和热闹的建房仪式都消失了,

当年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

在贵州与广西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
当然也有很多“无”变成“有”的。以前大家抱怨贵州山区交通很不方便,地无三尺平,甚至有“穷山恶水”之称。但现在贵州有了大量的高速公路,桥梁隧道,更有一个个巨大的水库。珠江径流量在中国河流中最大,水流落差也很大,因此珠江上游建了很多水电站,形成了很多水库,环境变得山清水秀,游客可以乘坐游船,在水库边的木头别墅住宿,享受贵州美食。所以水利设施的改善带来了贵州整体生态文明和经济模式的很大变化。
艺术中国:您在重回故地中,还有哪些您感受很深的地方?
王璜生:我还有一个感触比较深的地方就是贵州的册亨。当年这个地方破破烂烂,路面泥泞不堪,但在这样偏僻落后的地方,我们居然找到一家书店,我在书店里发现还有作家妥斯托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我就买了一本,当时印象特别深。
这次我们专门去册亨寻找这家书店。现在通向册亨的道路已经是多车道的高速公路,册亨新区也建了很多新楼。我们寻到老城区,在一处街角发现了一家新华书店,就是我记忆中的那家书店,里面还有个读书角。店主说书店是他们接手的,但这书店一直都存在着。虽然当下实体书店式微,但这家书店还能勉强维持,这也说明这一带爱读书的习惯一直还保留着。
新创作的触发点是1984年在珠江源头采集的植物标本
艺术中国:后来是什么原因让您想到要做“珠江溯源记”巡回展览?
王璜生:我的《珠江溯源记1984》编辑过程中,广西师大出版社希望在图书出版的同时,在他们的美术馆做珠江溯源的展览。这当然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我想,不能做成只是80年代珠江溯源的回顾性展览,我要做新的当代艺术作品来回应这段历史。从2000年底到2022年,我做了《珠江源植物图志》《珠江源植物采集》《远方与河》《骑走》《源头/活水》《远方与路》等六组比较大型的绘画、影像、装置作品,与1984年的珠江溯源写生、摄影等一起展出,这也是对自己生命的重新审视。

《珠江源植物采集》摄影 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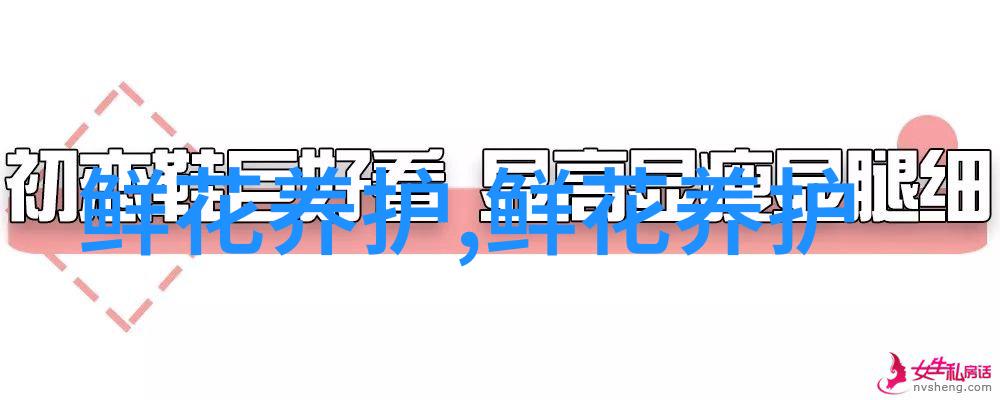
植物图志201028 水墨设色拓印 46x35cm 2020
艺术中国:您在“珠江溯源”系列创作期间正值疫情肆虐,整个世界停摆,当时您是如何想到将遥远的早期经历与当下特殊的现实进行触发与连接?
王璜生:当时我在整理资料准备新作品的时候,我在不断回忆或者重新感知过程中就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感受。我们曾经的生命跟我们当下是什么关系?重新回到珠江,又跟当年的经历有怎样的连接?用什么方式能够将我们对过去的一种追问表达出来?
思考过程中,我的触发点就是1984年我在珠江源头采集的一些杂花。当时就夹在信封里寄回来,我一直将这些植物标本保留在我的速写本里面。当我重新看到它,我一下觉得30多年前的这些标本就像化石一样,跟时间有关,跟生命有关,它重新唤起了我很多感觉和想象。
这些标本又很有形式感和物质感。我重新回到珠江源头采集植物,将新的标本跟我当年的标本产生联系,跟当下的艺术形式产生关系。
我使用水墨拓印的方式创作新作品。水墨和拓印都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同时拓印有科学的成分。我就使用银白黑墨尝试,银和墨之间有层次感,加上水的调和,它的颜色漂浮起来,墨沉在里面,特别立体和微妙,呈现出一种类似反转片的特别效果。

《远方与河》系列局部综合材料 2021年
艺术中国:您在“珠江溯源记”的水墨拓印的画面上手写了很多朦胧诗的诗句。80年代诗歌曾经与艺术界紧密相关,您在80年代就结识了江河、杨炼、马德升、黄锐等一批朦胧诗人和艺术家,但是当下艺术界似乎远离了诗歌,您在展览中对诗歌的表达出于怎样的思考?
王璜生:在巡回展第二站昆明的时候,一方面是展厅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也想在原有基础上往前推进一点,因此将作品转换成胶片,我在上面写上朦胧诗。
80年代这些朦胧诗曾经深深影响了我们,引导我们走出去,这些诗和我的生命记忆有关。诗歌有一种更为浪漫的情节,跳跃性的思维方式,包括诗歌对社会问题的追问,很天真但意象又很丰富。
诗歌比较浪漫的特点,遇到比较现实的社会,对我们这些已经步入很现实年龄的人来说,有时候会觉得跟实际想法差距比较大,我们现在看诗歌也相对比较少。
但是作为年轻人,我想大家要更为浪漫,更有丰富想象力,甚至更幼稚的想法。幼稚并不可怕,幼稚是生命必须有的童真纯净。
我不希望仅仅画非常柔美的东西,喜欢对力量的追求

《源头_活水》(榕树)2022
艺术中国:您的《源头·活水》将珠江源寻回的水在广东的土地中孕育新的植物,这是否象征在时代背景下,对我们原初生命力的呼唤与激发?
王璜生:我很难说想要激发什么,但是我个人的创作比较喜欢对力量的追求,对事物背后的一种张力的追求。
《源头·活水》这组作品是将源头的水贯穿在一个时间和地理的长河中,在珠江的出海口与这里发生新的关系。照片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我将珠江源的水做成瓶装矿泉水,带到广州的展厅。在展厅中,一方面观众可以分享源头的水,感受珠江源;另一方面,我将几百瓶“源头活水”矿泉水瓶口打开,每瓶插上一支广东的榕树枝,榕树枝很容易生根,用源头的水滋养广东的榕树,而这一阶段,正好广州发生砍伐榕树的事件,因此这作品也很有社会针对性。目前,这组装置作品收藏在广州华南植物园里,榕树枝一直长势良好,很有意思!

《源头_活水》(浮石湾)2022.1
另一部分是“浮石”。珠江的出海口有一个“浮石湾”,那里烟雾缭绕,水边巨石就像漂浮一样。我联想到小时候经常在海边游泳,看到泡沫和沙子凝固起来的“石头”漂浮的状态。我就找来这样的石头,借助珠江出海口的浮石湾,我做了一个海浪和浮石的作品。作品意象表达的是珠江的水从源头的涓涓细流,流经两三千公里,到了出海口形成汹涌澎湃的海浪,激起了这里的巨石“浮动”起来。水是如此的柔顺,但是水也能够将坚硬巨大的石头托浮起来。这是对力量和意志的一种呼唤与隐喻。

王璜生 《骑走》 纸本水墨拓印 1450x730cm 2021

王璜生,《风之痕》,影像,3'23",2020年
艺术中国:展览中《界》《风之痕》《呼/吸》涉及了铁丝网,纱布,氧气瓶等物象,它们蕴含着对生命既保护又有危险的意象,您对于这些材料的使用有怎样的思考?
王璜生:这是我一直想去探索的东西。我这么多年在美术馆工作,做过非常多当代艺术展览,我以前学习传统绘画,渐渐对当代艺术特别感兴趣,但是我对纸本绘画的上手感、直觉感比较强,审美也很认可。我想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一个切合点。《游·象》表现线条的时,从观念的层面,我希望是一种控制与自由、与自在的表达。而线条既要优美自在,又会出现铁丝网的感觉,我不希望仅仅是柔美的东西,想表达一种刺痛感,特别是它的芒刺。
后来我就开始关注材质,铁丝网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材质,做过很多铁丝网类的作品。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电视新闻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街头或者隔离的铁丝网,它构成了一个非常直刺人心的意象,暗含的文化符号内涵很强。
后来我又找到了纱布,用纱布包扎铁丝网,纱布的柔软和铁丝网的坚硬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关系。我又将纱布作为拓印转换成黑色、红色的水墨作品。纱布转换成水墨后,其肌理感非常微妙独特,也很有内涵意蕴。后来我又以“氧气瓶”“爆炸后的烟花残件”等做装置、影像、拓印等作品。

王璜生 呼_吸1 装置_影像 2000x900cm 2019-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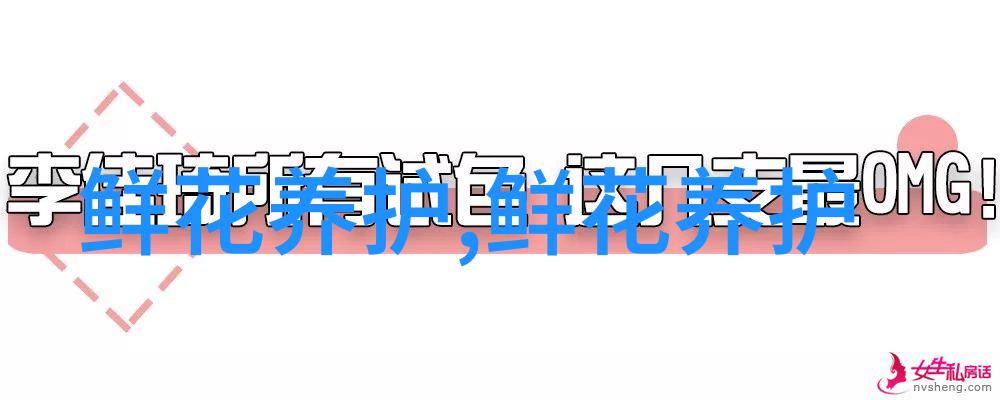
"王璜生:七重旅途”暨“从这里出发:珠江溯源记(1984-2024)巡回展/汕头站”展览现场,汕头美术馆,2024年

影像装置作品《界》
艺术中国:您的装置影像作品《呼/吸》,您敲击氧气瓶的画面和声音给人相当的心理冲击,作品是受疫情的影响而创作的吗?
王璜生:一直以来我可能对危机美学比较感兴趣,像我的“铁丝网”也好,“纱布”“氧气瓶”也好,我的作品都有这样一种危机意识。我当时做《呼/吸》的时候疫情还没来,2019年的三四月份,我经常去医院照顾家人,那段时间段我对氧气瓶感触特别深,然后开始做这样一类的系列作品。

《呼/吸·关键词》,王璜生、徐梦可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2月版
艺术中国:《呼/吸》展览是在疫情期间推出,近期您和徐梦可又出版了新书《呼/吸·关键词》,这本书的内容和形式都很特别,您能介绍下展览和这本书的关系吗?
王璜生:我原定是2020年的2月份在上海龙美术馆做《呼/吸》展览。当时疫情还没有发生,请柬都印好了。疫情到来后,我们将展览推延到2020年的8月。
《呼/吸》展览做完后,通常会做一本画册反映展览现场和策展思路,我希望以展览的新画册引发更进一步的思考。因此,我就找了中国美术馆的徐梦可博士,她对西方哲学文化很敏感,让她参与这书的编辑和写作,我和她讲这本书最好不要做成我的作品集,要有新的叙事角度和思辨理论性。她提出了“呼吸关键词”这个概念,将和生命与呼吸相关的27个关键词列进书里,例如“肺”“隔离”“远程办公”和“生物公民权”等。每个关键词有一段文字,又跟我的作品有关。当时也担心国内出版社是否能出版,后来广西师大出版社对这本书非常认可决定出版,现在中文版已经出版,英文版正在制作中。
优秀的当代艺术能够表达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
艺术中国:从您早期的珠江溯源到后来您在美术馆工作和当代艺术创作,都体现了不断突破舒适区,开拓新领域的勇气,吴洪亮馆长用“游刃”两字来形容您这种状态,您认为艺术创作中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王璜生:我在民生现代美术馆做《边界/空间》展览的时候,策展人巫鸿老师说我的作品是在不断逾越边界。我不会满足于固守一个东西,需要不断尝试新的事物。包括我做美术馆的工作,要做独立的学术坚持,还要有挑战性地将一个事情做成。
艺术创作上我们要坚持自身的探索,即对生命问题的不断追问。我觉得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可能充满危机,充满了矛盾和不平衡,包括伤害和死亡等等。归根结底艺术创作是对个体生命的自由表达和深度关注。

2006年,“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大型摄影国际巡回展在德国德累斯顿国家博物馆开幕(受访者提供/图)
艺术中国:您策划过很多有关个体生命和人文关怀的经典展览,您比较满意的有哪些?
王璜生:我做美术馆馆长很多年,做过很多人文关怀的展览。我感觉最成功的是2003年的《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摄影展,展览包含了1950-2000年600多件非常有力量的中国纪实摄影作品。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当时的冯远馆长亲自重新写前言,用很煽情的语言表达展览主题。后来展览又在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巡回展出,对学术界影响很大。
这个展览最重要一点就是作为中国的官方美术馆,提出了要反映和表达中国人的人性追求和个性张扬。
我认为,优秀的当代艺术应该是表达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具有思想与观念的内涵,敢于提出问题,有问题意识,具有艺术史的建设性,能够触动人的精神和情感,引发人们更多的感触与思考。因此,我做广州三年展便是抱着这样的态度。
另一方面,我在广东美术馆的工作,也注重对一些艺术史问题做研究性挖掘性的展览,即“寻找失踪者的踪迹”系列展览。历史上曾经有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因为种种原因渐渐销声匿迹了。这些艺术家对艺术史的重新挖掘梳理非常重要。我们不希望总是做大家耳熟能详的艺术大家展览,我们应该挖掘一些被历史,甚至被残酷的历史因素所淹没的人物。
当年我做“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及王子云先生的研究性展览,并收藏了考察团当年的一大批作品及成果,引起了文化界的强烈反响,也包括广东的谭华牧、赵兽、梁锡鸿等艺术家的抢救性挖掘性研究、收藏、展览、出版工作。
后来我到中央美院美术馆后,便开始做北平艺专历史挖掘与研究的展览,一年做一个专题,将中央美术学院与前身北平艺专之间关系的历史认真梳理清楚,这是我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我不太想去做那些大家炒得很红的东西。

"王璜生:七重旅途”暨“从这里出发:珠江溯源记(1984-2024)巡回展/汕头站”展览现场,汕头美术馆,2024年
艺术中国:今年四月份,“珠江溯源”巡回到汕头美术馆展出。汕头是您的故乡,这里保留了中原传统文化又有海洋文化的冲击,您觉得故乡对您的个性有哪些潜在影响?
王璜生:我觉得一个人一定脱不开他生长的土壤,我从小在潮汕长大,学习、工作、生活,一直到30岁才离开这里,之后又与潮汕有着非常多密切的联系,潮汕文化的好好坏坏多多少少在我身上都有影子。
从唐始中原地区的人就不断有往南方包括潮汕迁徙的,韩愈被贬到潮州等,这对潮汕文化的影响很大。潮汕保留了很多中原文人的儒雅文化基础,包括语言、饮食、手工等等。另外,潮汕地窄人多,竞争激烈,潮汕人必须走出去冒险,很多人都有出洋经商的经历。同时潮汕人也养成了精工细作,手脚灵巧的特点。这在艺术方面也有所反映,因为经济与商业的关系,画画人很多到上海求学,而心灵手巧,也使学习“海派”时,笔墨很有灵韵。
我身上还是有潮汕知识分子偏于儒雅的气质,但同时也属于敢想敢闯的。我做的当代艺术作品被认为比较有文气,但也敢于做一些当代文化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我80年代中撰写的长文《现代艺术:模糊化的民族性和多样化的个性》发表于《美术》1986年第一期。我认为民族性问题不用老挂在嘴上,不用怕没有民族性。别林斯基有一个论断,他说一个俄罗斯人生出的小孩,一定是黄头发和白皮肤,不可能是黑头发黄皮肤黑皮肤的。他其实在说民族性是始终存在的,你不用老担心民族性丧失了,或被改变了,被西方文化殖民了等等。一个人一定不可能脱离本民族的一些东西,它应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因此,我在文章中提到,现代艺术应该更多地鼓励和追求个性的表达。
艺术中国:您在广东美术馆和现在的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工作过很多年,对广东的当代艺术发展非常了解,您认为当下广东地区的当代艺术呈现怎样的状态?
王璜生:我觉得目前广东当代艺术的发展状态和全国有点相像,因为现在的文化气氛,没有构成较强烈冲击力的艺术,也没有一种特别的问题意识。
当年广东做得比较好的是“大尾象”工作组。他们的出现是在1991-92年,对当时广东迅速发展的消费社会特别敏感,提出的思考也做出了表达。随后,也被国内国际所关注,广东的批评家策展人,及早期的广东美术馆等机构,也构成了一种推动当代艺术发展的合力,因此,那个阶段广东的当代艺术还是比较有认知度和影响力的。广东一直有这样的特点,就是不少年轻艺术家各自有想法,也做出一些实验,不过,当下,区域性的合力与形象,包括展览、机构、市场、藏家、推手、批评家等,需要有整合的力量和新的突破。
(受访人:王璜生 采访人:刘鹏飞 资料来源:王璜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