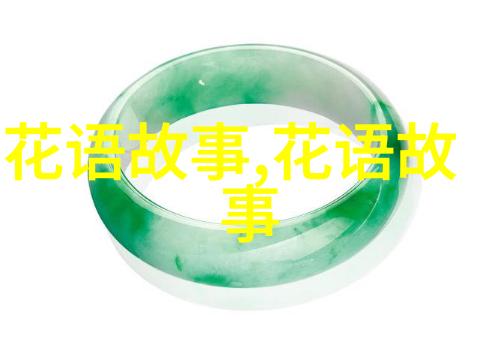谈王弼玄学对文人书画艺术兴起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代在民族历史上是一个大大的苦难时代,但在这个灾难深重的年代里,民族哲学和艺术却开出了极其灿烂的花朵,尤其是文人书画艺术,就在此时兴起,从此成了民族最具代表性的高雅艺术。然而,对于文人书画艺术为什么会在这个时代兴起,始终是一个令人既感兴趣又感为难的问题,尤其是它与玄、佛、道哲学的关系,更令人头痛,但若不深入地加以研究,总是令人为之感到遗憾的事情。纵览现代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能较为深入的似觉不多,因此仍需要大家继续努力化功夫。本文仅对王弼玄学对文人画兴起的影响谈点粗浅的看法,也许有助于同行们深入研究。 文人书画的兴起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与玄、佛、道时代新哲学的兴起,对文人书画艺术的影响,似乎更为直接而深刻。 曹魏正始年间兴起的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乃是民族固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创造与发展,它不仅为民族的儒学、道学和佛学交融合流铺填了道路,而且为民族本体论哲学走向高峰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对于“玄学”的特质,却至今仍被误解(笔者在几年前出版的《易老子与王弼注辩义》,深入地论述了王弼玄学的特质)。“以无为本”的确是“玄学”哲学的最高范畴,若因此而判定王弼玄学是唯心论,就大缪了。“以无为本”由何晏提出,而他在哲学上并无什么建树。而王弼的成功,是其依时代的要求,将“以无为本”作为方哲学的原理,来建立民族本体论哲学的认识论与方。自觉地从事这一研究,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它标志着民族哲学的发展走向成熟,这便是王弼玄学的伟大贡献。他所创立的认识论和方哲学,便是在他的《道德经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和《论语释疑》中所提示的:以无为本、崇本息末、崇本举末、崇本统末。“本末”问题虽然在方略中常常为人们所运用,但作为哲学原理来运用,只有王弼。由于时代历史的悲剧,王弼创立的认识论与方哲学,虽然未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这一点,从玄学深刻地影响了文艺理论和诗书画艺术,便可一目了然。 王弼玄学在西晋是被禁止流行的,至东晋才得以流布,开始对社会产生影响,(但王弼玄学与郭象的《庄子注》唯心论玄学则有本质的区别,不少研究者将他们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而到南朝宋齐间则在官学中取得了优势地位,与儒学文学、史学并列,称为“四学”。这便是东晋至南朝,文艺理论获得蓬勃发展,并达到空前水平的重要原因。如顾恺之、谢赫的画论,王羲之、王僧虔、萧衍等人的书论,刘勰、钟嵘的论文、诗论等等,至今让人仰之弥高。文艺理论的发展与成熟,自然大大地推动了文人诗书画艺术的蓬勃发展与成熟,因此而出现了象陶渊明、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象王羲之这样的“书圣”和顾恺之这样的大画家。一时间,诗人、书家、画家,呈现出群星灿烂的景象,其辉煌的艺术成就成了后人效法的典范。 首先来谈谈书法艺术。书法,被人们视为艺术,乃是东汉末年以后的事,大概是由于蔡邕等人的积极参与倡导。而在此之前,从事文字书写工作的乃是吏与工匠,贵族、文人是不屑一顾的,认为那是下等人干的事。而作为书画艺术,则服务于政教,并无独立的品格与地位。不过,书法成为民族的高雅艺术,在社会上取得崇高的艺术地位和声望,无疑与王羲之在行草书上的卓越创造和成就,有着密切的关系,惟有行书、草书,才能真正体现与发挥这门独特艺术的特质和艺术性。 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在书法艺术创作中,汉字作为文字的特点和意义,已被淡化与消却,成了抽象的无形之形的方块字线结构形体,书法凭借这一无形之形的抽象线结构形体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既有规律有无规律(有法、无法与无法之法)的无象之象的意象艺术。在一定意义上讲,书法是首先受到玄学的影响在艺术上获得无上的升华,因此也是最能体现王弼玄学思想精神的艺术。书法是一种无形之形、无象之象之“无”的独特艺术,的确是名副其实的“以无为本”的艺术,除了书法之外,似无艺术能如此深刻而形象地体现王弼玄学的精神。书法也因玄学的影响而使行书、草书的艺术性达到神奇超妙的境界,成了民族的也是东方的最具特色和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我们试看一下当时书论的一些主要观点。如南齐王僧虔的《笔意赞》有云:“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以斯言之,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这里所说的“神采为上”。便是要求书法须“以无为本”;“形质次之”,意在“崇本息末”;两者能兼之者,是要求能“举本统末”。如能达到这一要求,他认为“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方能达到。意思是书家在书艺创作时必须忘我,随心所欲,随情所之,随意而发,心、手、书合一,任意气而为,不知书而书也。这便是以无为本,超以象外,得意忘象也。如其言:“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章”也。书家要求达到这种境界,是非常困难的,唯王羲之酒醉书《兰亭序》似已达到这种奇妙的境界。 梁元帝萧衍更有极其精到的论述,如其《草书状》有云: 疾若惊蛇之失道,迟若绿水之徘徊。缓则鸦行,急则鹊历,抽如雉啄,虞如兔掷。乍驻乍行,任意所为。或粗或细,随态运奇,云集云散,风回电驰。及其成也,粗而有筋,似葡萄之蔓延,女萝之繁萦,泽蛟之相绞,山熊之对争。若举翅而不飞。欲走而不停,状云山之有玄玉,河汉之有列星。厥体难穷,其类多容。婀娜如削弱柳,茸拔如袅长松,婆娑而飞舞凤,宛转而起蟠龙。纵横如结,联绵如绳,流离似绿,磊落如陵。暐暐晔晔,奕奕翩翩,或卧而似倒,或立而似颠,斜而复正,断而还连。若白水之游群鱼,藂林之挂腾猿;状众兽之逸原陆,飞鸟之戏晴天;象乌云之罩恒岳,紫雾之出衡山。巉岩若岭,脉脉如泉,文不谢于波澜,义不愧于深渊。传志意于君子,报款曲于人间,盖略言其梗概,未是称其妙焉。” 这里萧衍以自然天地山川风云、草木鸟兽虫鱼等可见的各种变化形象作比喻来描述草书的情状,已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他说这还只是“盖略言其梗概,未足称其妙焉。”的确,书法艺术作为一种“无形之形,无象之象”的一种抽象艺术,不仅给书法家创作以极大的想象空间和随心所欲的书写自由,而且也给欣赏者以自由的想象空间和各自不同的艺术感受。如萧衍在他的《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评钟繇书曰:“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评王羲之书曰:“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这种以象喻意的书评手法,如王弼所言是兔与蹄,鱼与荃的关系,象以尽意,藉以更好地揭示钟王之书的超凡书艺的特色和成就,也为更好地启发引导观赏者得意忘象,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欣赏去感受。书法艺术这钟特殊的传情达性之抽象性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悟性,使书法的艺术境界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玄妙卓绝的地步,因此在民族的文艺殿堂里确立起崇高的地位。其次来谈王弼玄学对“文人画”兴起的影响。如顾恺之的画论“以形写神”论和艺术创作之“迁想妙得”论,亦是王弼的以无为本、崇本息末、以象尽意、得意忘象论的很好体现。顾恺之是就人物画创作提出的,认为画人主要是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他说:“四体妍蚩,本无阙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顾是无锡人,“阿堵”是古代无锡方言,指“这里”眼睛。顾恺之认为人的眼睛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内在精神,与“眼睛是灵魂的窗户”之意差不多,所以他往往画人数年不点睛,以求更好地表现出人物的精神风貌,并在艺术上达到更高的境界。因此,他在创作时非常强调“迁想妙得”论。如他画裴楷象,虽形貌极似,却总觉缺少裴楷那种少年老成、英雄超群的气质和神韵;他苦思多日,灵感忽出,迁想妙得,遂在裴楷画像颊上添了“三毛”,实际上是加画了三胡须,于是精神遂增,人们看了都觉得好极了、更象了。裴楷年轻,颊上还没有胡须,如何会加了胡须反而更好更象呢?这里我们可以联系今天舞台上周瑜与诸葛亮的形象设计,便能明了。赤壁之战,周瑜三十六岁,诸葛亮二十八岁,而在舞台上,周瑜潇洒英俊,是位青年将军,而诸葛亮则是位留着长须的老谋深算的老道人。舞台人物形象设计也是着眼于更好地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也可谓是以形写神,以无为本。顾恺之在裴慨颊上加添了胡须,便能更好地表现裴楷的少年老成,“隽朗有识具”的特质和风韵。顾恺之画嵇康时,曾说:“手挥五弦”的形象容易画,而要画出他“目送归鸿”的神韵则困难。“以形写神”不仅是文人画水平大为提高,而且也是判别绘画艺术水平高下的重要准则。 至南齐谢赫的“六法”,终于确立了“文人画”的基本准则。其“六法”是:“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谢赫“六法”虽然没有同时代刘勰的《文心雕龙》那样的弘篇巨著,论述全面而透彻,但其简约精微,深刻严整,并不亚于《文心雕龙》。“六法”于绘画艺术,乃是千古之法,为历代画人所重。刘勰、谢赫在文艺理论上的伟大建树,显然是深受了王弼玄学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王弼玄学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以至本书的篇章结构也采取了王弼《周易注》的大衍历数,共四十九篇,终篇为结论,合五十篇。是遵崇王弼的以无为本、崇本统末、以一统众之意也。他把王弼的认识论与方十分透彻地运用于他的理论创作中,务以道为本、举本统末。正如他所说:“思无定契,理有恒存。”故须“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总本”篇。)“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章句”篇)他一再阐述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并在《序志》中抨击当时的各文学家文艺理论舍本攻末、不得要领的弊病和缺陷;批评文学诗歌重形式不重内容的严重弊端和不良文风。他运用王弼的“以无为本”、“得意忘言”、“得意忘象”的理念,努力高唱神韵、神思、风骨、骨力、情采等对文艺创作的重要性。从《文心雕龙》看来,谢赫“六法”的创立决非偶然,同样是受到王弼玄学的影响与推动,使文艺理论水平获得空前提高的新形势下才创立的。谢赫“六法”的本末关系非常清楚,第一法“气韵生动”是本,其余五法是末,是谓以本统末、以一统众也。气韵生动,是绘画作品的灵魂和神韵,是艺术作品创作和评判的主要标准。其余五法多是技巧问题,但技巧对绘画艺术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造成“气韵生动”艺术效果和高度的基础和手段。所以一法与五法的关系,既要求画家以无为本、崇本息末,又须能崇本举末、以本统众。这样的辨证关系便对画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要求画家有极高的艺术技巧,而且要求画家于画外有深厚的学识与道德修养。如谢赫在《古画品录》中,以“六法”为标准来评判古今画家,便将名画家顾恺之贬到第三品里去,认为他的画虽“格体精微,笔无妄下”,技巧很高,但“迹不逮意,声过其实”。说明顾恺之虽然极重“以形写神”,但其画迹仍未达到理想的境地。“迹不逮意”,是指他的作品囿于象内,未能达到绝言超象、气韵生动的更高境界。这无疑与顾恺之时代王弼玄学对社会和艺术影响的程度尚浅相关,人们对艺术的理解还有待提高,文艺理论尚处于初创阶段,虽有真知卓见,却构不成严整体系。正如刘勰所批评的,各家皆偏于一隅,甚至舍本攻末。谢赫则尊陆探微为第一人品第一人,评其画为:“穷理尽性,事绝言象。”为上上之品,是屈标第一品第一人。谢赫如此推崇,是坚持“以无为本,崇本息末”的原则,强调了“气韵生动”这第一法的重要性。“气韵生动”因其难以言喻,历来为人所头痛,似近于刘勰《文心雕龙》所论的“道”,是人生之道、社会之道、自然之道、文艺之道,在艺术表现为一种生动的气韵感,绝言超象,似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一种“无状之状、无象之象的无。”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在艺术中的确有那么回事。王羲之酒醉中写出了《兰亭序》,成为千古行书第一,而他自己酒醒之后也叹为观止,之后他一再重写,却无法达到原先的艺术水平。我们今天面对着这篇得道之书,也只能感叹其神奇超妙,不可思议。古今许多优秀的书法家、画家,都有类似情况,这种兴来绝笔,不仅艺术家本人不可再,后人同样难以超越。文人画艺术这种现象,向为后人所称道和追求。至宋以后,评论家不仅将“文人画”与工匠画截然分开,而且还在文人画的队伍中分出作家画、画院画、院外画;又将画列为神、妙、能、逸四品,并将逸品置于神品之上。这虽然与佛老思想影响有关,但仍未脱离刘、谢等文艺理论的主导作用,“以无为本”的王弼玄学始终影响并推动着“文人画”向高层次的艺术道路迈进。 从以上所论,王弼玄学对文人书画艺术兴起和发展的深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本文只是作一简略的论述。至于玄学与佛、道哲学的互相关系及其如何交互影响文人书画艺术,则更为复杂,但却十分重要,有待于大家深入研究予以揭示。时下人们对传统文人书画艺术或褒扬有加而故弄玄虚、或贬之过甚,恐怕都与对玄、佛、道与文人画艺术的关系的理解肤浅有关。因此,理论上急需攻破这一难关,以利于人们对传统文人书画艺术有一个正确而深刻的理解,以求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其优点,为创造时代新艺术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写于一九九八年)